走向国际化大都市的西安,最大的变化就在盛世长安,知道这是个人偏见,因为每次回去浪,都是光往山里钻,《卖炭翁》至今还能背诵几句哦,那一天,南山脚下《绿水园》的相会是我们一贯团结友爱凝聚力的大融合。
《 南 山 秋色 》
文/ 王潇然
夜宿山峪,享受着寂静中的秋凉,漫步山间的小路,伴着稀疏飘落的细雨,一股冰润清透的感觉,便轻轻穿透了薄薄的短衫,而林梢上的一抹暮色,也顺着飘起的衣角,把初秋的丝丝清寒默默地又蔓延进了身体。
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传来,带着一路贴身行走的星火,在路人的唇齿中忽闪着点点紧随的夜光,让落满夜露的小径蜿蜒得愈加幽暗。走近时,相继一声轻咳便互不惊扰得擦肩而过,前面就剩下了一段只有自己的山路。
很久没有了这种宁静的感觉,即使是孤身独处的时候,喧闹的市声也让人不能沉实,而今天的夜晚,尽管还缺少了些许的月色,但却除却了一身的烦嚣,心情轻飘飘的只剩下了一丝淡淡的思绪。寂寥的山野里,也停驻过一些曾经寂寥的斯文儒生,然而却留下了许多从来就未曾寂寥过的章句。
王维在月满的秋日踩着星光而来,写下了“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名言,也如我一般切身感受了“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现实体会。岁月流转中,一些寂寂寥寥的往事和空空落落的浮华,如今都已不知散入了谁家的竹篱木窗,而诗文中那些“晨起动征铎”的人,却还一直都在蔓延着自己“客行悲故乡”的不了情结。从《送别》中,我也尝试着轻轻打开一扇日暮后的柴扉,而眼前却早已不是了当年的情景,只是诗人悬在空中的那个挥扬的手势,还依然在滑动着日月轻尘染就的霜痕。
城门前,迎面清亮的山影,搅动着无数文人的情怀。祖咏吟诵阴岭渐逝的馀雪时,只用了一抹林表映现的霁色,就让长安空蒙上了一层浓浓的“暮寒”,平添了一种冷艳中的光鲜。城山相依,默默地互相诠释着一种无言的亘古依恋,成为了古都至今还最为标致的风景。
日前曾与熊召政小聚,这位名噪南北的荆楚雅士也一样怀揣着一份对南山的眷爱,直言南山对于长安就像老家与村口的槐树,倒让我也一时感同身受。走在下班的路上,迎面如屏的南山在斜阳的映照中,常常会现出一副清俊与刚毅的表情,用一种周身发散的熠熠神色,引领着我每每走向回家的路。
风吹云清,雨过月出。秋枝又摇曳着夜色,溪水也婆娑成了一潭情深的老酒。掬一捧在手,触摸着掌心里的月光,让自己就陶醉在了自己的指间。当我再张开手指的一瞬,如同一支阅尽沧桑的青樽在岁月里悄然开裂,水就变成了酒,酒已酿成了一串星辰的泪珠,又重新撒落成了脚下的一地月光。
《 天都太乙 诗意南山 》
文/ 王潇然
秦岭在长安城南面的这一段叫终南山,为什么叫终南有许多种说法,但无论是那种说法都少不了传说的神话,而这些神话也就让这座山带上了一些仙气。山上的佛寺和道观很多,佛教中华严宗和真言宗的祖庭,还有道教的发源地楼观台,更是给这里的神性增添了不少。古代文人崇尚仙风道骨,而进了终南山,身上立马就会由此而沾染上一些佛道之气,增添了身上脱俗傲世的底蕴,让书卷的气息更为浓重。所以,终南山自然就会吸引一些崇尚淡泊的雅士在此卜居,而一些政治上失意的文臣武将,也常常看破了红尘躲进山里归隐,以去除内心的浮躁和功名利禄的贪念。
姜子牙可能是在秦岭里隐居的最早的能人了。他的隐居其实就是一种包装,拿个没钩的鱼竿钓鱼,弄得玄玄乎乎的,主要是为了能够以此来引起周王的注意,结果还真的给应验了,最终也就实现了封神的理想。后来,有些人就开始依样画瓢,也学习他的做法,使归隐一下子又变成了一种沽名钓誉的手段。
人说相府里面好做官,一点也不假。虽不完全都是因为人熟好办事,但起码也是因为机会多。只要有能耐,给上一点阳光就能灿烂了。在终南山里隐居,有许多人其实打得就是这种主意。终南山靠近国都,隐居的消息自然容易让朝廷知道,而一旦得到了皇上的关注,肯定也就有了被召用的可能,迎来封官进爵的转机。
唐代的卢藏用,早年很背,曾多方求官不成,属于怀才不遇的一类。出将入相是大多读书人的理想,而他却仕途多舛,总是不得志。尽管他使尽了所有的高招,但还是一无所成,最后便拿出了杀手锏,选择了一条在终南山里隐居的路子,效法古人以退为进。结果,不久就达到了目的,受任为了左拾遗。相比之下,司马承祯在终南山里的隐居却要纯粹的多,他没有一丝功利的想法。唐玄宗本来也想请他出来辅佐朝政,而他却淡泊名利坚辞不受,执意要坚守那种闲云野鹤般的淡雅生活,一心向道,唐玄宗也就只能作罢了。唐玄宗早期信佛晚年崇道,尤其是痴迷道家谋求长生不老的丹术,而司马承祯经过多年的隐居修炼,道行也确实有了一点心得。对于这样的得道术士,唐玄宗既不好强求,也不敢怠慢,同时也出于对人才的尊重,便专门御批了一笔专款给他盖了一座别舍,让他专心抄校《老子》。修编经文还真是一个两全之策,既满足了司马承祯的愿望,也为自己积累了功德。而对于道家来说,这又更是一种责无旁贷的义务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司马承祯自然也就乐意效力了。等他完成了任务到长安去复命的时候,偏巧碰见了卢藏用。两人寒暄了几句后,卢藏用抬起手向南一指,开着玩笑说:“那里面确实是有一些好处的呀。”意思是说能够得到皇上的器重,就是隐居到了南山的原因,真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味道。司马承祯对他很是不屑,便不无讥讽地说:“是啊,依我看,那里还真是一个做官的捷径呢。”由此也就有了“终南捷径”的来历。
隐居文化源于崇道。道观多在山中独据一峰,占尽山水之利,彰显了道法自然的教义。道士们都是山中活着的仙,高逸缥缈。隋唐以来的文人学子常慕此风,尤其是求取功名不成,就隐居终南,以求东山再起。因此,在终南山中修建别业修身静养一时就成了文人们趋之若鹜的时尚。而幽闭的寂寞总要消解,他们便借助诗词把山水怡情和胸臆心意抒发出来,这样一来,终南山就借助别业又多了一层文字的装饰,最后就形成了一种独有的隐居、别业和诗词三位一体的文化孪生景观。今天,我们就可以由隐居入手研究诗人,再从别业走进他的诗词,同时,还能够在诗词中了解到他们当年的生活实况。
从李白的《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春归终南山松龛旧隐》和储光羲的《终南幽居献苏侍郎三首》及《贻阎处士防卜居终南》这些作品可以看出,他们也曾隐居过这里。正是这些卜居的隐士和传诵的诗歌,让终南山在人文精神方面与长安构建起了一种独有的关系。
皇室权贵精神空虚,生活奢靡,修建别业不仅是悠游林泉,更重要的是标榜身价,所以建筑格调多追求华丽纤秾,以满足虚荣之心态。如太平公主的南庄别馆,赵彦昭就在《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中做了详尽的描述:“主第岩扃驾鹊桥,天门阊阖降鸾镳。历乱旌旗转云树,参差台榭入烟霄。林间花杂平阳舞,谷里莺和弄玉箫。已陪沁水追欢日,行奉茅山访道朝。”
京城文人多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为信条,修建别墅多少都带有“隐退”的色彩,故其建筑格调多追求恬适宁静,以达到“独善”的境界。如韩愈的韩庄,“时见水底月,动摇池上风。清气润竹林,白光连虚空。”
王维的辋川别业,更是其中的典型,虽然辋川早已再难觅它的踪迹,但诗中记录的风华却犹然兀自耸立在我们的眼前。
从山口进,迎面是“孟城坳”,山谷低地残存古城,坳背山冈叫“华子岗”,山势高峻,林木森森,多青松和秋色树,因而有“飞鸟去不穷,连山复秋色”和“落日松风起”句。背冈面谷,隐处可居,建有辋口庄,于是有“新家孟城口”和“结庐古城下”句。越过山冈,到了“南岭与北湖,前看复回顾”的背岭面湖的胜处,有文杏馆,从“文杏裁为梁,香茅结为宇”中可以看出,这处山野茅庐,其南山岭环抱,其北湖水回绕。馆后崇岭高起,岭上多大竹,题名“斤竹岭”。这里“一径通山路”,沿溪而筑,有“明流纡且直,绿筱密复深”句,用一弯溪水、一条山路状其景色。缘溪而行,曲径通幽处另建“木兰柴”,这里景致幽深,有诗说“苍苍落日时,鸟声乱溪水,缘溪路转深,幽兴何时已。”溪流之源,跟斤竹岭对峙的山冈,叫“茱萸片”,大概因山冈多“结实红且绿,复如花更开”的山茱萸而题名。翻过茱萸片,为一谷地,有“仄径荫宫槐”句,题名“宫槐陌”。登冈岭,至人迹稀少的山中深处,题名“鹿柴”,那里“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鹿柴”山冈下为“北宅”,一面临欹湖,盖有屋宇,所谓“南山北宅下,结宇临欹湖”。北宅的山冈尽处,峭壁陡立,壁下就是湖。从这里到南宅、竹里馆等处,因有水隔,必须舟渡,所以“轻舟南宅去,北宅渺难即”。欹湖的景色是,“空阔湖水广,青荧天色同,舣舟一长啸,四面来清风”。如泛舟湖上时,“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为了充分欣赏湖光山色,建有“临湖亭”,有诗这样描述:“轻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尊酒,四面芙蓉开。”沿湖堤岸上种植了柳树,“分行接绮树,倒影入清绮”,“映池同一色,逐吹散如丝”,因此题名“柳浪”。“柳浪”往下,有水流湍急的“栾家濑”,这里是“浅浅石溜泻”,“波跳自相溅”,“汛汛凫鸥渡,时时欲近人”,不仅描写了急流,也写出了水禽之景。离水南行复入山,有泉名“金屑泉”,据称“潆汀澹不流,金碧如可拾”。山下谷地就是南宅,从南宅缘溪下行到入湖口处,有“白石潍”,这里“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跋石复临水,弄波情未极”。沿山溪上行到“竹里馆”,得以“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此外,还有“辛夷坞”、“漆园”、“椒园”等胜处,因多辛夷(即紫玉兰)、漆树、花椒而命名。
王维长于诗画,园林造景别具一格,淡雅超逸的陌园亭馆,空旷幽静的柴屋岗岭,诗情画意的片滩湖泉,处处体现出一种朴素自然而合于哲学的园林境界。
据说西汉的李广被解职期间也曾归隐过一段。李广是文帝时期的“飞将军”,立有战功无数,但却始终未能封侯,留下了“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典故。相比之下,王维在辋川结庐就要纯粹多,而他留下的诗词也最多。王维与裴迪的《辋川集二十首》,每首都是同名诗,主要以山林胜景为客观描写对象,把山水田园的静谧明秀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了中国山水田园诗高度成熟的标志,在唐代乃至中国山水田园诗歌发展史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为后人树立了诗歌典范。除此之外,他写的还有《山居秋暝》、《终南别业》和《终南山》等等。时间的确能够称得上是一位端庄的史官,经过日月的沉淀洗练,再怎么美艳的楼堂馆所也会像诗人的长衫一样褪色毁损,留下来了的,却是这些历经风沙的吹刮而不朽的诗句。
诗圣杜甫曾到南山寻访隐居的高士,写了一首《玄都坛歌寄元逸人》,诗曰:“故人昔隐东蒙峰,已佩含景苍精龙。故人今居子午谷,独在阴崖结茅屋。屋前太古玄都坛,青石漠漠常风寒。子规夜啼山竹裂,王母昼下云旗翻。知君此计成长往,芝草琅玕日应长。铁锁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萧爽。”如今,步着诗圣的后尘,还可以寻访到当年的玄都坛,鸟瞰山中的景色,五谷中的七里坪残存着一些星星点点的古栈道遗迹,从李太白“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的诗句中,感受到一丝千年的古风。
相对于世俗的长安城市井而言,风景秀丽的终南山绝对可称之为世外桃源了。西安城北枕龙首原,南望终南山。终南山拱卫着长安城,成为地理上的屏障。隋唐两代的文人墨客负笈千里,求取功名之余,面对着这高耸的山峰,怎能不生出些许的感慨?
古时长安城中的高大建筑不多,只要举头南望,南山便清晰可见。山所富有的宁静自守的气质、昂扬向上的的姿态,以及蓬勃鲜亮的性格,都很容易使人生出一些感怀,文人们便常常藉此借诗词抒发胸臆,寄情言志。南山因诗词而闻名,诗词又因南山而源源不断,后来竟使南山都成为了秦岭的一个代称,而终南山和中南山还有太乙指的也都是秦岭。
南山离城40公里,像老宅门前的影墙,给老城增添了一层怀旧的深度。天气清朗的日子,南山就端立在眼前,一副宽厚浩大的身姿,随时都能吞纳进所有关注的目光。3000年前,人们就在《诗经·小雅·节南山》里描述了这样的风景:“节彼南山,威石岩岩。”高大不仅仅是威严,也有神秘,神秘便可以裹藏一些想象,寄托一份心念,《诗经》的《秦风》就记载了那时曾经萌生过的这种向往:“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在奴隶主统治的时代,南山没有例外的归属王室所有,老百姓是不可能想进去就能进的去的,守着葱葱郁郁的山林却食不果腹,他们怎能不生出一些念想。画个饼充充饥,说一说咽口唾沫,也算过了一把嘴瘾吧。
南山,在文字上显然是一个名词,名词就能清楚表明事物的属性。但在画作里,南山却是一个形容词,能够把场景的神气张扬出来,使以南山为背景的长安更富内涵。而在诗词中,南山又像一个副词,能够渲染作者的情绪,加强文式的气氛。
从祖咏《终南望馀雪》中我们读到的就是诗人对长安城的忧思。
当时,年轻的诗人满怀建功报国的凌云壮志,自东都洛阳来到了帝京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早闻长安城南的终南山以其独特的风姿横亘关中,广绵千余里,又恰逢终南山刚刚降过雪,于是读书之余,诗人欣然沿北坡而上,饱览了雪后终南山的秀丽山色。这样,一首流传千古的传世名作便在酝酿之中了。当在科考中看到“终南望余雪”的试题时,便用清丽的文字和忧国忧民的情怀,抒写了这首千古传诵的好诗。“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诗人从侧面落墨,虚处生神,林表的霁色,因余雪而增“明”,城中的暮寒因雪消而更烈。不见“余雪”二字,而尽得风流。
韩愈的《南山诗》也写到了平时眼中的南山:“尝升从丘望,戢戢见相凑。”终南山一年四季的变化,几乎纤毫毕现地呈现在长安人的视线之中,而他在《出城》中“暂出城门踏青草,远于林下见青山”的句子,更是远眺南山的情景。孟郊的《游终南山》,写到:“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还有张乔的《终南山》:“带雪复街春,横天占半秦。”这些诗句写出的又都是南山这一自然景物对人的心灵和精神的陶冶与净化。一泓清泉,数株幽兰,都可以对人有所启迪。
李世民的《望终南山》、王维的《赠徐中书望终南山歌》和张元宗的《望终南山》,都是终南山带给诗人的感触。
南山中还有许多有名的去处,如紫阁峰、仙游寺、五台山、太白山等,也都留下了许多诗篇。李白的《登太白峰》、司空图的《次韵和秀上人游南五台》,多不胜举。孟郊在《游终南山》中用一句“长风驱松柏,声拂万壑清”,写尽了山林松涛的怡情。
中国人自古就有着对诗词如宗教一般的虔敬,一首诗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可能也只有在中国才有。诗词的意境美和富含的智慧,既能使我们获得心灵的愉悦和精神的享受,还能带给人许多的启示,读出人生的道理,这便是我们中国所特有的文化根基。我们用文化信仰代替了西方的宗教崇拜,不像宗教那样不管是要求来生,还是为了保平安,总是都会有所图,而这种信仰,却显得空灵和纯粹,高洁和脱俗。从小的时候背记唐诗开始,我们就一代一代接受着这种文化陶冶的洗礼,所以也就形成了一种堪比宗教的文化崇拜,而秦岭的诗就是这种文化崇拜的产物。
西方即使再怎么伟大的名山,恐怕也不会有哪一座能够容纳下如此之多的闲雅名士,因为他们就没有那样的隐居文化和诗词文化,缺少了对于文化的那种神祇般的膜拜,也就不可能凝聚住几千年文学关注的目光了。而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就已经开始记录,其中的《国风·秦风》中十篇即有一篇《终南》,《小雅》七十四篇有其三,即《南山有台》、《节南山》、《信南山》。唐诗中有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孟浩然《岁暮归南山》,以及柳宗元《终南山》,还有北周虞信的《陪驾幸终南山》、欧阳詹的《秦岭诗》,以及杜甫、杜牧等人的《子午谷》等。如此密集的笔墨,除了秦岭还有哪一座山能够受用的起呢。因为秦岭才有了长安,秦岭又因为长安才有了诗,而诗却又让这老城青山的峨冠博带在零落成泥之后,还仍然镌刻着山河、雕镂着人心。
转载自:未名花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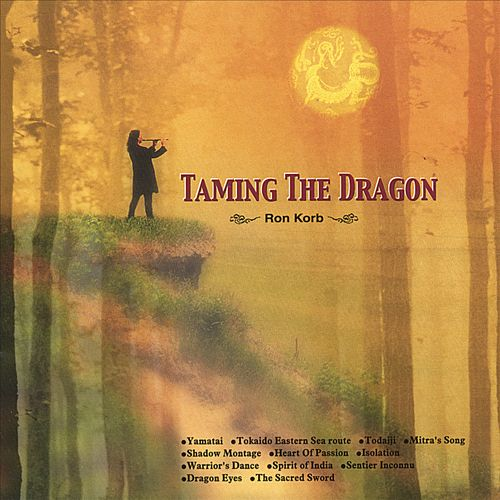

评论(1)